朱文杰揭秘,北教场与教场门之谜(下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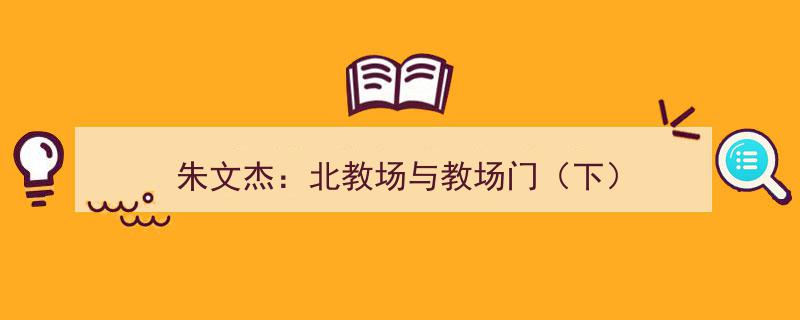
朱文杰的《北教场与教场门(下)》可能是关于北京北教场及其周边历史、文化或建筑的研究文章。以下是根据这个标题可能包含的内容进行的一个概述:
---
"北教场与教场门(下)"
"引言"
在上一部分中,我们介绍了北教场的历史背景和它在军事、政治和文化上的重要性。在这一部分,我们将深入探讨北教场周边的教场门及其在历史长河中的演变。
"教场门的起源与变迁"
教场门,又称北安门,是明清两代北京城北部的城门之一。它位于北教场北侧,是通往北郊的重要通道。教场门的设立,最初是为了方便军队出入北教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成为了北京城北的商业和文化中心。
在明朝,教场门是军事要地,驻有大量官兵。到了清朝,这里逐渐演变成了繁华的商业区,各种商铺、客栈、庙宇等设施纷纷涌现。教场门附近的市场,因其地理位置优越,成为了北京城北最热闹的地方之一。
"教场门的建筑特色"
教场门的建筑风格具有鲜明的明清特色,城楼高大雄伟,城门洞宽敞,两侧设有箭楼和角楼,形成了坚固的防御体系。城楼内部则装饰华丽,雕梁画栋,体现了皇家的威严。
"教场门的历史事件"
教
相关内容:
那时,我刚回西安不久,担任《长安》文学月刊社编务主任,事情繁乱紧张,分管财务、编务、美编及发行。尤其是发行,当年刊物发行量低,亏损严重,四处欠账。和谷评价我那时“乐于琢磨书西刊杂志的装帧印刷,甚至发行。看起来他很木讷,或者暮气,半天工夫会沉思于一件小事。但同时,他常常步履匆匆,风风火火,像有一百件事情等着他去做。”确实,当时我就处于这种状态。在编辑部受聘的作家黄河浪说:“文杰是不动,就沉默如山,动起来,就急如脱兔。”
接着不到一年时间,刊物发行到三十万,一举扭亏为盈。不但还清旧账,还拿出一万元,为市文联机关购置了全新的办公家具,桌、椅、书柜、书架、脸盆架,以及供中午休息的床等。接着,又在西安承办了《小说月报》三北(华北、西北、东北)编审工作会议。其间,我负担的事非常之繁重,多亏了美编陶虎、会计秦友君、出纳杨燕,还有第五建平,以及黄河浪,一个个让我指挥得团团转,不辞辛苦地跑前跑后,干这干那,一下让我轻松了不少。
先说美编陶虎,在杂志社,我们合作密切,配合默契。当时我极力想改变刊物面貌,内在文字质量是主编和编辑的事。我这里就是如何包装刊物。当然首先是封面,这就得依靠美编啦!陶虎艺术水平高,鉴赏能力强,出手不凡,他设计出的封面给人眼前一亮,焕然一新的感觉。当时《长安》改名《文学时代》,一是想追求时尚潮流,二是怕让人误会为长安县办的刊物。因为社会上当时很多人不知道文联、作协为何物。我们参加一些社会上的会议时,就发生过不少次尴尬。你说是文联的,人家一登记,会上介绍成“残联”的;你说是作协的,人家诧异:“做鞋”的,咋跑到这开会呢?这真不是虚构。当时《文学时代》封面设计一般化,陶虎回忆他把我拿给他的一幅天鹅摄影艺术照设计到封面上,刊物一印出,受到内外一致好评。后大家统一了认识,长安是古代汉唐之长安,又恢复《长安》刊名,陶虎专门为改回的新《长安》,设计大唐标志大雁塔上封面。一亮像相又是好评如潮。让我不由击节赞叹!又古朴高雅,又时尚新颖。陶虎回忆,当时已调进文联创研室的《长安》老编辑贾平凹一见,也连声夸赞,说这才像个样子,附合一家市级刊物的身份,一扫过去封面设计的陈旧死板没内涵。接着1987年春节前我正好去扶风、宝鸡、凤翔一带采风组稿,记得和诗人渭水、当时在凤翔师范当教师的评论家张志春,一起骑自行车去六营村,拜访老泥塑家胡深,买了件一尺多高的凤翔泥塑《坐虎》,回来让陶虎拍照上了封面,又引来一阵惊叹。因为当时西安没几个人见过如此美轮美奂,大俗大雅的凤翔泥塑。
当年我和陶虎的另一件事就是整天跑印厂,为封面版式设计,取送校对稿,催进度督印。记得有西北三路的省印,和平门附近的西安市一印,跑的最多的是李家村铁路局印刷厂。当时和印厂打交道事最麻顺。我和陶虎还去了甘肃天水一家印过钞票证卷的国营大厂,处理遣留问题。顺便一起上了趟麦积山,当时我正被卷入风波漩涡之中,正遭人出卖诬陷,身处困境。于是回来写了一首诗《麦积山石窟》发了点愤慨。诗中写道“满山的灵眼/感悟不到麦子的金黄/……石窟中的众佛仍千篇一律的笑着/笑我痴得顽固/笑我不避身侧的冷箭/仍旧九曲八弯地攀缘……飞天舞出独有的风姿/装点我行程的寂寥/石山生出双翅/摇一路花雨/但也阻止不了有人耸肩谄媚的表演/终究,舌头包不住牙齿/是人是妖/都逃脱不了/麦积山洞开的慧眼 ”。

陶浒(虎) 如今是老城记忆手绘图名家
还有当时正好铜川煤矿的业余作者第五建平在《长安》编辑部培训学习期滿。于是,我留下他给我帮忙,连带着也给和谷主持的西安市作协文学讲习班帮忙。而后来第五建平也成长为一位有影响的作家,还被西安邮电大学聘为客座教授。他辛勤耕耘,著作颇丰,几十年来出版了小说、诗集、散文等十多本,有《硬汉狂想曲》《失调》《家庭风暴》《狂想的旋律》《尘土飞扬》《绿色花瓣》《第三代移民》《上网时代》《山里有个家》等。尤其是一百三十万字,三卷本的长篇小说《绝境》。想着当年满嘴撇着醋溜普通话的第五,被我嘲讽为四难听的“刮锅、打娃、驴叫唤,外加第五建平的普通话”的第五,如今却让我刮目相看再相看啦。
1986年酷热夏天的最难熬,记得我和从铜川来《长安》文学月刊暑期学习的刘平安一起,各人卷一片凉席上招待所三楼楼顶纳凉过夜,这当然比窝在房子吹电扇强多了。刘平安回到铜川,先后任铜川市作协副主席、铜川文物旅游局副局长。后调到西安,先后任陕西省文联办公室主任、人事处长。他从教场门起步,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在教场门完成了他创作的第一本诗集《缄默的黄土地》,并邀我写了序。
我在序中写道:“我们一起睡楼道,睡楼顶,一是躲西安使人无法抵御的酷热,一是彻夜长谈。谈趣闻,谈逸事,当然更多的是谈诗歌了。这段日子,我们的友谊是因诗而联系起来的。天虽然热,可刘平安总是在默默地读诗,总是在默默地写诗。不几天功夫,看到他拿出那一大沓诗稿,我惊奇了,连他自己也惊奇了!说这几天写的诗比他以前写的诗总和还要多。面对这个表面沉静而内心火热的刘平安,我深深被打动了。他是属于内秀那一类,大量生活的积淀,使他磨好了刀刃,好像接受到某些暗示或者碰撞吧,他顿悟了,一下子找到了自我,诗情好像一河的水都开了。”
以后,刘平安还出版了诗集《山那边人家》,散文集《烟云长路》《途中》等,多次获省级文学奖,已成为陕西的一位小有影响的实力派作家。
说到西安酷夏的这种露天过夜,还是我六十年代住白鹭湾时卷凉席上城墙睡觉经历的继续。那年月,西安大街小巷的老百姓上街道马路沿沿上睡觉也是夏季三伏天一道特异的风景。
而我的文学道路在这里进入了快车道,出版了自己第一本抒情诗集《哭泉》,正式成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虽然我在铜川时就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了1983年中国作协陕西分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享有正式会员选举权,但入会手续却是到教场门后才办的。在这里,我和一批作家成了风雨同舟的战友,有商子雍、子页、和谷和黄河浪、陶虎等。在这里,我结识了在诗歌创作上赏识我、指点我的老诗人沙陵,是沙陵老不持偏见,或“独持偏见”为我的诗集《梦石》写评论,给我以前所未有的“溢美”和鼓励。
在这里,我结识了一大批全国的文学朋友,有获茅盾文学奖的周克勤,有老一辈的木斧、雁翼、黎焕颐、李牧歌、雷霆,还有雷抒雁、叶延滨、杨景民、包川、冯传德、水渭亭、张雪杉、李霁宇、李发模、楼亦林、张德强、许德民、马建、李老乡、嵇亦工等。这些人生路上遇到的难得的师友,给我的无私帮助,至今都令人难忘。
四教场门南口那一棵古槐树,是一棵很有点儿传奇色彩的隋槐。虽然这棵古槐早已不见踪影,但历代史书里均有记载。
据传当年,隋文帝长安选址建皇城时,发现这一带有村子名杨兴村,预兆他们杨家该兴,于是以此为中心建城,建成时就名叫大兴城,以此处一棵大槐树为标志,槐树就屹立于皇城第一横街的广阳门(唐承天门)西边。后来在横街两侧栽种了一排槐树,可是,这棵古槐与新栽植的树行不齐,有司请示欲将此树伐除,隋文帝知道后急令保存。到了唐代,这棵槐仍因挡道面临被伐,传说唐太宗李世民知道后,令妥为保护。民国时期任过陕西通志馆馆长的宋联奎编撰《咸宁长安两县续志》时,曾亲自到这一带查看,发现这棵隋槐仍在。

1930年前后至1952年,我们家租住在北教场巷21号二十多年。我的爷爷朱子训在西安永盛西酱园当店员, 1934年逝世于此巷。那时家境极困难,全靠奶奶和姑妈在家做针线活养家。家中留有奶奶和姑妈做绣活的剪纸粉本。我曾按着家传留下的花样,在我十七岁时的1965年照葫芦画瓢剪过不少,可惜如今只留下两幅,其中一幅“梅花”还刊登在陕西教育出版社《关中民俗》一书中。
我姑妈两子两女,都比我年长,尤其是我大表哥张健儒,一直是我父亲教育我学习的榜样和做人的标杆。他1954年十几岁时,从西安卫校招到甘肃参加医疗卫生队。我父亲说:你哥那时太艰苦了,吃的苦条子面,一次在甘南藏区一位牧民被熊抓翻半张脸,他抱着伤者的头给缝脸,但这位牧民终于因受伤太重死在他怀里。他就这样一下坚持了十年,从西安招去的十几名队员,实在受不了跑得就剩下他一个,还被评为先进,被保送上了兰州医学院,又入吉林医科大学学习,是中国最早一批学习防原子弹核辐射的医生。毕业后分配到兰州炼油厂职工医院,成了闻名一方的名医。后担任兰州炼油厂职工医院副院长。
那时,我们家太困难了,我的父亲名朱洪泰,1932年十五岁时就到孙蔚如任师长的国民军十七师修械所当学徒;1933年至1936年在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修械所当技工;1939年至1940年在西安西京机器厂当钳工。1940年后一直到1952年父亲在家中开私人铁工坊。1950年我父亲曾任北教场这一片街巷的抗美援朝主任委员、西安市第六区人民代表。后第六区与第三区合并为莲湖区。1952年搬到北马道的神器库巷。
五我是六十年代挨饿的三年困难时期过来的人。让如今年轻人想不通的是,记忆中很多都和吃有关。而教场门的饸饹,这个享誉陕西的名吃,是这里给我影响最深的吃食。在西安市文联《长安》文学编辑部时,经常有外地文学朋友来,就点教场门的饸饹,所以,我吃饸饹基本上是陪客人。而且物美价廉,客人满意,替我省了不少银子。
教场门饸饹起源于清末民初,历史太久了。最初创业者是渭南县渭河北吕家村孟兆武。1932年,年仅二十岁的孟兆武来到西安开饸饹馆。先在南院门第一市场,以后就搬到教场门了。
荞面饸饸古时称“河漏”,有六七百年历史。元代王祯《农书•荞麦》载:“北方山后,诸郡多种,磨而为面或作汤饼,谓之河漏。”教场门饸饹只所以盛名久著,主要是选料制作都极精细,多选用渭北各县及千阳、陇县、长武一带所产新荞麦,现磨现压。特点是光细滑溜,筋韧有骨,香辣爽口。西安民谣中有:“你爸的扁担压饸饸,你妈的胭粉擦的多。”压饸饸,需经专用工具——饸床压制而成。

图/西安吃喝玩乐逛
1986年夏天我接待一位蒲城籍老领导,他就专门点教场门饸饹,我刚说,不行不行,咱们上西安饭庄。他就连忙拒绝,还说,我们蒲城出的英雄杨虎城当年就爱吃教场门饸饹。
这么多年都没吃过了,文友陈嘉瑞在博客上发了一篇写到教场门饸饹的博文,我留言说,哪天相约上一起去教场门品尝一下当年老字号的正宗风味。于是,2013年10月的一天,我们就一起去红埠街西口教场门饸饹店吃了一回,我也算故地重游。需要说明的是,教场门饸饹店实际店址现在属红埠街。这里当年从北教场巷至狮子庙街(今为北广济街)亦称教场门,而教场门之名能留下,甚至代替北教场巷,可能全靠这饸饹店了。
可惜的是,原先店面已改换门庭,只是在门前东侧保留一亭子间,号称教场门饸饹,吃的人大多,都是慕名寻来或旧地重游的人了。饸饹馆已萧条得不忍卒观,只是口味还有一点。我以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吃食,年轻人哪里会喜欢又油又辣的热饸饹呢?有一次,我文联同事商子秦带儿子来这里,让儿子吃他小时最爱的豆花糕,谁知儿子咬了一口就不吃了,还揶揄他爸:你们当年咋就爱吃个这?!
我不服气,后在接待一位上海年轻的美女老板,领她品尝回坊小吃。于是在吃了麻酱凉皮、羊肉饺子正餐后,给她买了一份豆花糕。谁知这开始还有点儿矜持傲慢的女子,吃了一口就毫不掩饰地直喊:“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这是我吃的天下最好吃的美食!”我又为她买了一斤,让带回上海。那料到搡眼贪嘴的她回到酒店当晚把这一斤豆花糕全消灭了。豆花是豌豆加柿饼做的,不好消化,胃疼了一晚上。但回上海还给我打电话说:“朱老师,感谢您!”
 六
六教场门东口有两条朝南的巷子,一条叫郭签士巷,“文革”中改为光明巷;一条叫狮子庙街,南到麻家什字,“文革”中叫了风雷路,1972年成为北广济街一段。
封五昌的叔祖父是戏剧家封至模先生,他著文说:民国三十三年(1944),封至模先生在一些好友、社会贤达的支持下,变卖家产,筹集经费,于这年冬天创办了上林剧院,封先生任院长兼编剧及导演。上林剧院院址在民乐园东。抗战后期,上林剧院与刘文伯先生主持的晓钟剧社合并,组成新的董事会,由寇遐任董事长,马平甫、韩绾青等任董事,并更名为“西安私立晓钟剧校”,由封至模先生任校长。剧社设在广济街北面的狮子庙街,演出剧场则在社会路。培养出的秦腔名角演员,如任哲中、萧若兰等。
封至模先生早在二十年代初期,就开始戏剧活动,是我国话剧运动早期开拓者之一,同时对京剧、豫剧,特别是秦腔艺术,在理论、教育、创作、实践和革新诸多方面,卓有建树。
他还是夏声剧校(京剧)、陕西省戏曲专修班创始人,及西安饭庄、阿房宫电影院、西安实验话剧团的创始人之一。封至模先生在易俗社其间,创作的《山河破碎》《还我河山》两剧于抗日战争其间在北京上演,在全国引起了极大轰动,鼓舞了抗战中的军民。1937年6月13日《全民报》报道,《山河破碎》在北平怀仁堂演出盛况说:“观众之多,足无隙地,无票遭拒于门外者大有人在,观众欢迎的情绪,诚为仅见。”《山河破碎》何以如轰动?该报道深刻地指出:“当此国难严重之日,实于宋朝无二致。宋时君昏臣懦,畏敌如虎,因循苟且,只图贪生,抗敌之士不能容,奸佞当权,卖国误国,卒至沦于异族,在民族史上留一污痕”,而“此剧写历史的伤痛,促民族的觉悟,振聋发聩,去懦警顽,实对现时之中国当局下一针砭。方今举国民众,抗敌殷切,故亦极欢迎此抗敌救国主义之民族佳剧也”。
封至模先生一生著书无数,给我国戏剧研究事业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如《秦腔声韵初探》《中国戏曲大词典》《秦腔剧目汇考》《秦腔概论》等。

封至模先生
说到回民食品,第一号的就是羊肉泡。我有幸品尝到羊肉泡顶级厨师做的泡馍。先是在铜川遇上曾在西北局机关给刘澜涛做过羊肉泡的姚师、王师,他们在西北局撤销后1969年分配到铜川,在大同桥口一家泡馍馆掌勺。1973年时,我在铜川歌舞团想编一个煤矿井下摸黑武打的戏,正巧西安易俗社,当时叫西安市秦腔一团在铜川演出,我就联系请团里两位在“文革”前演过《三岔口》的武生演员,为我们示范任堂惠和刘利华摸黑武打的戏。示范完了我请两位去吃羊肉泡,说师父曾在西北局做厨师,进过中南海做羊肉泡。又给王师说,来吃泡馍的是西安易俗社的演员,王师马上兴奋地说,他当年随易俗社在北京和全国巡演一个多月呢。王师出来一见,果然是熟人,忙进去让换清油,专门为我们用不兑水的原汁骨头汤特殊加工。那天易俗社两位老师都说吃到真货了,我也感觉那天泡馍比平时要香得多。
再就是一次我和子页、商子雍等几位作家到狮子庙街北头一家泡馍馆去吃羊肉泡,进门后见店口坐一身材魁梧,长髯飘飘,风度极潇洒的老人。我问已很熟悉的店主,这是谁?店主笑答:“我家老爷子,八十八岁啦!”并说,他老爷子解放前是马鸿逵的家厨。又忙给老爷子介绍这几位是西安市文联的作家。三说两说,我们中最年轻的黄河浪张口让老人家露一手,正赶上老爷子兴致来了,立马笑眯眯地进去掌勺给我们一人做了一碗。味道自然正宗,此后,也自然成了我吹嘘的资本。

朱文杰(右)与商子雍
2006年时,一次商子雍兄打来电话请我到高新区一新开的大概叫伊兰什么的清真大酒店去吃羊肉泡,说厨师才从北京中南海回来。我赶去后,掰完饼递进去时说:我的这份不要油,子雍兄忙说他的也不要。这里潜台词是要用上好的羊肉汤泡。不一会,厨师出来了,连说今碰上吃家了,得见一见。于是,我又把前边经历的吃过谁谁谁做的羊肉泡给这位才从中南海载誉归来的师傅吹嘘了一番,以证明自己这个“吃家”还是蛮够格的。当然不忘奉承师傅一句,你是我遇到的又一位进过中南海给国家领导人做羊肉泡的顶级厨师。

图/西安吃喝玩乐逛
本文经朱文杰先生授权刊发